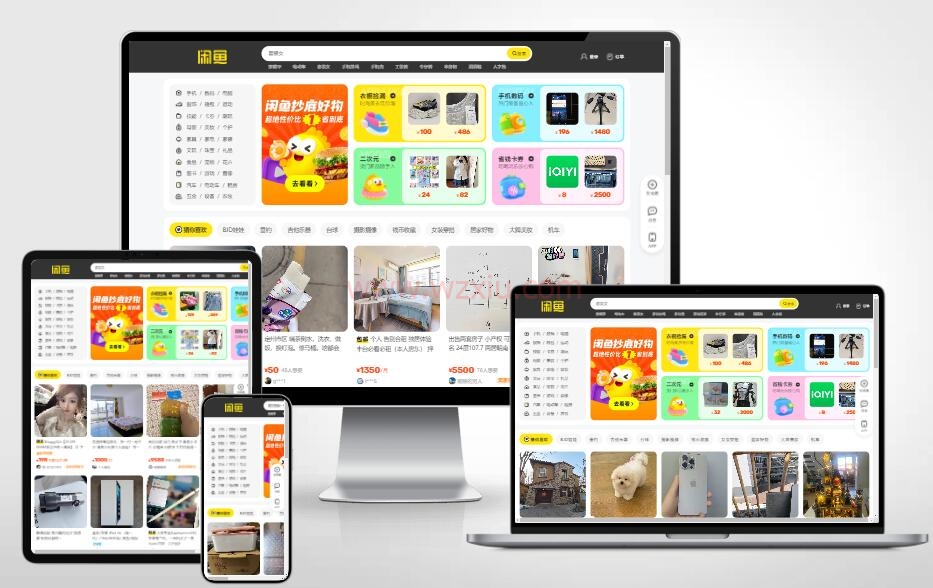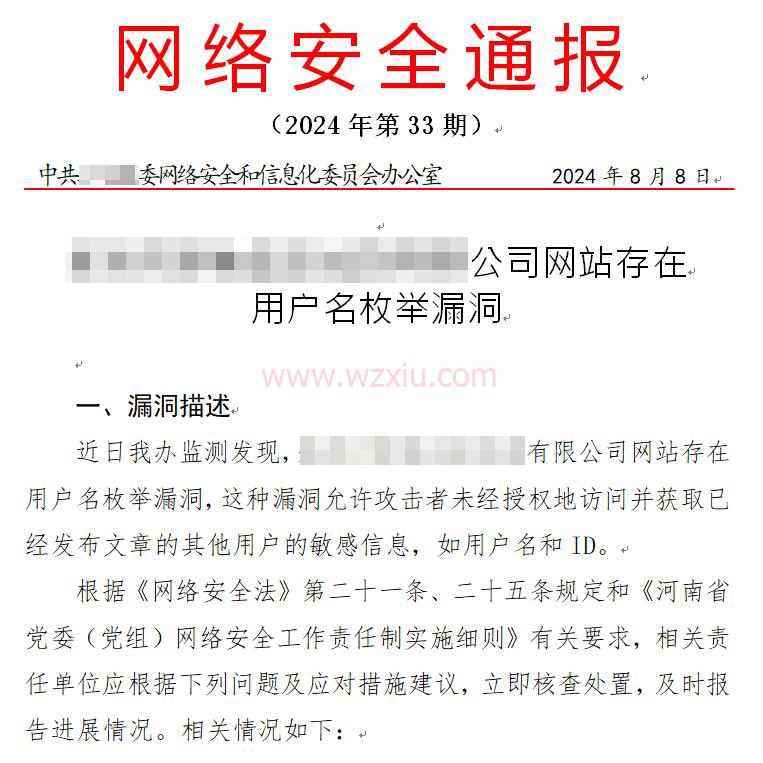原标题:在会所当了两年公关少爷,出来后觉得灵魂都不是自己的!
“成为什么,或什么都不成为。”这是我的好友张某在踏进白马会所前跟我说的最后一句话。在这之后,他将成为一个只被称作威廉的夜场公关职员。

【故事文章】在会所当两年公关少爷出来后觉得灵魂都不是自己的!
威廉祖籍达州,来自通川区的一户老旧居民楼,他十七岁那年就跟我说过自己的未来梦想是成为一名合格的四川公关。去危机中斡旋,在权色里迂回,到人群内化干戈为玉帛,也在风雨来临时敢于顶在所有人的前面,成为一种圆滑的光荣也成为一道背影的苍茫。但当时我是对公关这个职业没什么概念的,他说,我听,我就觉得奥特曼应该多半也算是地球的一个公关。

【故事文章】在会所当两年公关少爷出来后觉得灵魂都不是自己的!
所以到现在,我也一直会对公关这个角色存在着不少的尊重,尤其在灯红酒绿的夜店卡座,如果有一个姑娘跟我说她是公关,那我就会敬她一杯,说感谢她的付出,才换来了社会的安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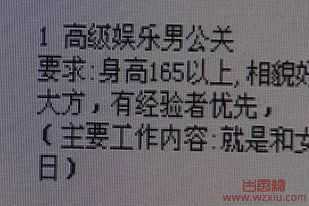
【故事文章】在会所当两年公关少爷出来后觉得灵魂都不是自己的!
公关并不丢人,威廉告诉我。因为细分下来的话,公关实际上也分很多种。有危机公关,艺人公关,财务公关和一些娱乐公关。他属于后者的衍生。只供职在一些笙歌艳舞的场地,但掌握的技能基本涵盖了前面说的所有公关的所学。

【故事文章】在会所当两年公关少爷出来后觉得灵魂都不是自己的!
根据他的经历,鬓发双白的阿姨是目睹过他摇出六个六豹子的,在二十几个公主面前,他也是被铝罐的百威砸开过发际线的,一晚上到手过八万,因为客户维护他也在神州租车下单过半年的凯迪拉克。

【故事文章】在会所当两年公关少爷出来后觉得灵魂都不是自己的!
相比我整天在公司喝着加浓美式码字的生活,他是精彩而颠簸的。但作为一个公关,威廉恨过,也爱过。用他自己的话说,唯独他从入职的那一天起他就没有打算后悔过。
“比起成为一个优秀的车间干部,我靠这个能往家里寄些钱。”他告诉我。

【故事文章】在会所当两年公关少爷出来后觉得灵魂都不是自己的!
成都不是他的家乡,他甚至也不知道九眼桥和望平街发生过什么风雨。他作为在场者流窜过很多场所,从金天下KTV到豪情洗浴会所,除了待遇上的不同,那些光鲜的姐姐和年迈的叔叔甚至在两个分别不同的场所关心过他在刚刚过去的冬天里有没有穿暖。

【故事文章】在会所当两年公关少爷出来后觉得灵魂都不是自己的!
但他只是个公关,对于这个城市来说,他也只是一个公关。在很多次扫黄打非的时期内,他甚至也可以被订正为一个无家可归的浪人。而每到这种时候,他都会带着一些他生命中的点滴来到我的出租屋内来暂避一下风头。

【故事文章】在会所当两年公关少爷出来后觉得灵魂都不是自己的!
威廉很喜欢一位李姓的姑娘,那是他在夜巴黎时认识的一个经济学博士,比他小两岁。从互加QQ到威廉用半个月的工资为她在香港定下一间高级餐厅时长不过半年,日常的大部分时间,威廉则都会选择在早班时早退一个小时去和李姑娘聊天。

【故事文章】在会所当两年公关少爷出来后觉得灵魂都不是自己的!
从市场导向对美股曲线的影响一直聊到昨天夜里没消化完的猪脚饭对早餐味道的转变,他们的聊天一直保持着同样的节奏,她在开始时是他的老师,结束时他成为了她的注脚。
他们在很长一段时间后的见面也是如此,威廉因为工作时染上的脏病拒绝了她在一次酒后的相拥。借口说自己在老家已经有了相亲,她骂威廉畜生,但只有威廉知道是自己选择成为了她的注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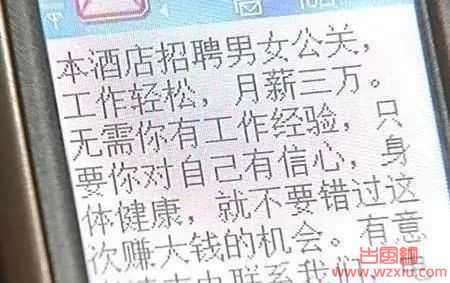
【故事文章】在会所当两年公关少爷出来后觉得灵魂都不是自己的!
不过其实威廉成为公关的时间实际上并不久,他做公关的时间加起来可能没有超过25个月。在这之前,他也曾短暂的和我拥有过一个同样的梦,我们曾相拥对月亮发过誓,说未来的文坛里一定要有我们两个新兴而稚嫩的双雄。

【故事文章】在会所当两年公关少爷出来后觉得灵魂都不是自己的!
只是他的流俗要比我想的来得更快,也更彻底,再加上一些原生家庭的影响,他对声色犬马的选择始终还是大于了对文学的热爱。他仍然坚持在写诗,每年过年时也会托我把他手写的家书和礼物带到他的双亲面前。而每当他的父母向我询问他的近况时,我也只是年复一年的按着威廉的意思,说他仍然在从前的工厂,做着一个光荣的车间干部。

【故事文章】在会所当两年公关少爷出来后觉得灵魂都不是自己的!
后来他也离开了,在一次真正的成为张某之后。威廉去了另一家工厂成为了一名真正的光荣的车间干部。一次在老家的见面中,他穿着劳保服,理了平头,他的父母不再因为他曾经每个月打回来的五万块钱骄傲,他也失去了曾经随时挂在脸上的神情。在分别时他对我说,他不知道以后会怎样,但他爱过做公关时的荒谬胜过不做公关时的荒谬。

【故事文章】在会所当两年公关少爷出来后觉得灵魂都不是自己的!
我想,我应该是可以完全理解的。
毕竟,公关这个职业始终会被懂它的人崇拜着,像威廉;也被不懂它的人崇拜着,像我。毕竟,成为什么,或什么都不成为嘛。